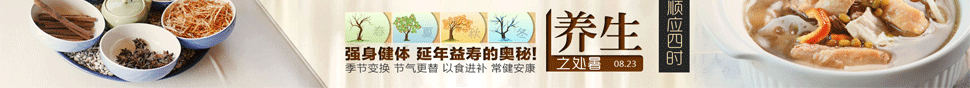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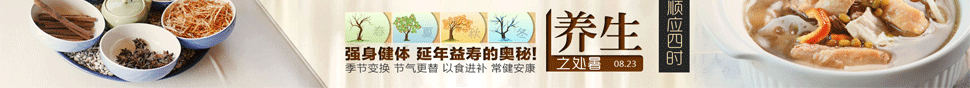
梦回依约向后院
一分老人
有如读过小说的昨天,或婉转,或激宕,回环往复在阳光斑驳、树影婆娑的老屋后院。
半个下道地,多半在东厢位六间两层老屋,住着我家、隔壁叔家和阊门叔家。不多不少,每家两间,不全是祖上传下来的,里面有买卖的均衡。
东厢老屋与堂前叔家住的堂屋构成L状,世代围着一个不完整的道地,各家几无从容而艰难地生活着。西厢位只是低矮的猪舍,阊门只有断垣残壁,搁几个破旧的盆、罐,种上韭菜、葱蒜。不怕荒芜,太阳花正伺机而发,松叶牡丹爆盆,用尽夏天的热情,装点简陋的门面!
东厢老屋的后门,隔着一条狭窄的石子路,是由北向南,三叠落的院子。每个院子不大,六七十平方米,都是乱石嶙峋的矮墙围绕,院子的归属不完全和厢屋对应,隔了狭窄的一条路,外面便是大千世界!
小山村有悠久的历史,曾几何时,它是清溪岸异常发迹的村落,人口聚集,生活富庶,还有族人在朝中当差。不料明清时期,几次干旱,连遭火灾,加上瘟疫侵袭,村民死的死,逃的逃,偌大的村庄,一下子败落了,只留下几户人家形影相吊,苟延残喘。
风水轮流转,附近原来弱势的村庄变得强盛,以致纷纷把坟墓做到败落村旁边,贪恋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风水宝地。当然,风水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大凡昧着良心强占豪夺,用村舍和农田做坟的,其后代不怎的,甚至不乏断了香火。
后院最北即最高的院落,我家拥有大部分,除了建有牛栏、猪圈外,还有一块空院地,上有两株颇有岁月的老梅树,寒冬腊月,万花凌寒盛放,华盖屋顶。“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对老家旧屋的怀念,这诗句是最好的写照。隔壁叔家在我家牛栏的北面搭灿建有猪舍。院的东边,则是阊门叔家管业,用作蔬菜地。再外面就是“四箩”了——平平整整的田园,由旧屋基改造而来。
中间院落,有几穴坟墓,从未见过其后人来扫墓,农业学大寨时被人平了坟头,种上苦楝、香樟、梅树、桑叶、梨树、枇杷、棕榈、乌桕、喜树等,树木未高大时,隔壁叔家种些棉花、金针(黄花菜)等经济作物。后来,树木葱茏,棉花种不了,金针(黄花菜)也渐渐变疏。继而杂草丛生,瓦砾成堆,虫鸣鸟叫,成了散放猪、鸡的乐园。村里人有一种说法,牲畜蹦哒可以驱散阴气!
最南院落,地势最低,集中做了露天粪坑,足有五六口之多。从前露天粪坑一般很简单,即一口七石缸,半埋地下,上搁坐马,再考究一点三面围上挡雨又遮羞的草披。遇到大暴雨或洪涝,粪坑总有尿粪溢出,周边土地相对肥沃,不知何时,旁边多了一丛雷竹,春天雷笋破土而出,陡增勃勃生机!
鲁迅先生笔下有意趣横生的百草园,我们后院亦是,常见的紫苏、车前草、鱼腥草世袭生长。一株万年青,静静偎依墙角,人生苦短,没有人知道它的实际岁龄。一蓬落落跌(接骨草),春天来了,总是在枯枝落叶间又唤醒新绿。一盆芍药,种在破缸里,小时候我们误把它当成国色天香的牡丹,“欹红醉浓露,窈窕留馀春”。最多的莫过于兰花,均从本地山上移植而来,在破罐残盆里塞些碎瓦砾,再铺上香灰土,春秋两季会开出扑鼻的清香。回过神来,只不知曾经种过的兰花里,有无“宋梅”“龙字”国兰双璧?老围墙上,在岁月抖落的尘埃里,长满了雀梅、络石、马蹄筋、紫叶红花酢酱草、红萼苘麻、鸡冠刺桐、金钱草、狼尾蕨等等,差不多可编半部《本草纲目》了。抬头望,老树枯藤边,还攀爬着叫碎骨补的附生蕨,非常耐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是从非常遥远的古代走来!
浓荫蔽天,自然成了小动物的乐园。可爱的小松鼠冲着成熟的枇杷、梨子来,即便到了冬天,苦楝籽也足可让它饱餐一顿。喜鹊喳喳枝头,我们总愿意和谁家的喜庆事儿联系起来。每当七夕来临,我们仰望天空,银河鹊桥,似乎都是从这里捡拾枝条去叠筑的。牛栏、猪圈上稻草披和几只稻草蓬,无疑是麻雀的天堂,它们成群结队把家安在上面,遗落的稻穗便是它们的粮仓。高耸入云的喜树树杈上筑着雁窝,雁窝里不只有鸟蛋,而且还有我们童年的飞翔期待。成双成对的蝴蝶,在院子里或上下或来回舞动着,我们打心里认定是梁祝情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阊门叔不知从哪里弄来留声机,梁祝音乐响起,更是情景交融!
记得初夏时节,异常闷热,我们管即将要下大雨的天气叫“涨黄热”。这时喜欢垂钓的人,准会带锄头到后院挖竹蟮(蚯蚓)。肥沃的土地,湿润的环境,非常适合竹蟮生长,常常一锄下去,能挖到好几条大小不等的蚯蚓。当然,也会误挖出土狗(蝼蛄)、蜈蚣、蚂蚁、白时虫(蝉蛹)来,原来地下世界并不寂寞、孤独!运气好的,还能挖出银元、铜钿来。不知情的,以为是古墓葬品,其实不然。
在离村不远的后山脚,我们当地人叫大岭脚,高山厚土,有很多古墓群。在村民挖土烧制砖瓦时,曾挖出精美的陶瓷、凤冠、灯盏等葬品来,被识货的人打着拿去鉴定为由,一去不返。祖上曾经的荣耀,如今只烙在刹那的记忆里!那里面并无银元、铜钿等随葬品。哪么后院的银元、铜钿等宝贝疙瘩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母亲后来给出答案,这些东西是她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时光回到“文革”初期,各地开展“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群众运动,后来纷纷成立“红联总”“县联总”准武装组织,说是“文攻武卫”,其实很多是挟私密斗,包括宗族械斗,泄愤恶咬,当地臭名昭著、惨绝人寰的“宁天三”事件(指完全捏造的发生在宁海、天台、三门县交界地区的所谓反革命事件,造成多人命案,涉及许多无辜干部、群众),就是例证!
我外公早年突然患病去世,留下羸弱的外婆和她的八个子女,大多未成年,最小的还在襁褓中。我母亲排行老二,豆蔻年华,本应人前撒娇。但为了全家老少活命,她毅然作出决定,只身去上海滩打工。
到了上海,举目无亲,先是墙弄头帮人缝缝洗洗,依靠微薄收入生活。个中吃得苦,只有她自己知道,到死她都不肯与我们说,或许是不堪回首,或许是不让我们“吃”二遍苦。后来,经好心人介绍,到一个资本家家里,给尚未成年的大小姐当丫环。生活境遇改善,母亲有时会说这段经历。可是,这段时光不长,即将迎来上海解放。
主人家虽然和善,但给人当丫环的生活毕竟寄人篱下。主人家怕共产党革他们资本家的命,准备举家南迁香港。我母亲则说好回家,并买好了返乡的船票。这张船票要上的船,就是年12月3日,震惊中外的触雷沉没、夺命无数的“江亚”号客船!
母亲是如何逃过一劫的?原来母亲照顾大小姐非常体贴周到,日久情深,大小姐听我母亲说要返乡,就哭得稀里哗啦,死活不肯。资本家就开出优厚条件,劝我母亲去退了船票,与他们一起去香港。就这样,母亲与其说是捡回了自己的一条年轻的生命,不如说是讨回了一家老少勉为其难的生活保障。
后来,母亲随主人家到了香港,过了一段时间,资本家又怕解放军打过香港,决定继续南迁。我母亲打定主意,这次不能再漂泊异国他乡了,一定要返乡照看老少。主人家可以说是仓促搬离,金银细软,特别贵重的带走,一般的家什物品留给我母亲处置,算是在上海开出优厚条件的兑现。主人家小姐取下自己头上的一枚银钗送给我母亲作留念。
我母亲拿了工钱和家什物品处置所得,从香港乘船,经上海返回老家。不知情的人,误以为我母亲发了“洋财”,耿耿于怀。殊不知,这是我母亲背井离乡、漂洋过海,辛辛苦苦换来的一点血汗钱。据母亲说,大部分交给了我外婆,用来照顾弟妹的生活。一部分后来与我父亲结婚后买了后院北边一块地。不久这块地被土改了,重新分配给我家、隔壁叔家、阊门叔家使用,农业合作化后转作自留地。
这样一来,所剩银元、铜钿不多了,加上人民币的使用,银元、铜钿只能私下变现或作彩礼、压岁、镇宅等用,母亲平时不会轻易去触碰,而是小心翼翼地珍藏着。
“文革”开始,村里那些造反起家,心怀叵测的人,开始盯上我家即所谓我母亲的“洋财”。他们打着“破四旧”的旗号,有计划、有预谋地展开“攻势”:先开会部署,有与会人员到我家向我父母“好心”通风报信,说当夜要入宅搜查,有人悄悄蹲守我家门前屋后观察动静。我父母不知是计,趁着夜幕,把仅有的一点银元、铜钿,暂时掩藏在后院隔壁叔家的金针(黄花菜)地里。不料当夜并无人入宅搜查,父母觉得不妙,去后院隔壁叔家金针(黄花菜)地一看,暂时掩藏的银元、铜钿早已不翼而飞。知道是坏人使招,但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又能怎样呢?父母强压心头怒火,互相劝慰,互相开导,就算是捐给了那些生活无着落的人。
电闪雷鸣,狂风暴雨,不知是要发泄我父母的心头恨,还是要浇灭我父母的无名火?山洪挟着泥沙,翻黄倒浆,横冲直撞,把个后院沧海桑田。冲刷成沟的地方,泥鳅、黄蟮游动,时不时搁浅,做了鸡鸭的美宴。冲积成扇的地方,好像在有意掩埋不堪回首的蹉跎岁月!
雨过天晴,我们几个小伙伴,围在沙堆里,用稚嫩的小手挖呀刨呀,说是要找到七色彩虹的根。因为,从稍远地方看来,彩虹的一头就插在这里,如长龙饮水。
挖呀挖,我们挖出了碎瓷片,毛蚶壳,挖出了麻将牌,三万、七万、一束、九筒、发财??继续挖,我们挖到了一片厚玻璃碎片,在阳光照射下,折射出七彩来,大家可高兴了,原来我们真找到了七色彩虹的根!
小孩的心,是永不干涸的井,始终填不尽好奇的世界。大伙漫无目的接着挖,我想洗手休息片刻,不料在洪水冲沟里发现了“定海神针”!拔出来一看,小小的,我拿到我母亲跟前问这是什么东西。我母亲眼睛一亮:“这从哪里来的?”“我从后门院子水沟里挖出来的。”我如实回答。“对喽,这是我们家遗落的,今天失而复得。不要与人说,银钗以后留给你们传世。”显然母亲怕这根银钗得而复失!
我很想回到童年,回到自家后院继续淘宝。但是,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都像刨出来的麻将牌一样凑不齐了,许多旧事,只好埋在心底,种在梦里!
有一点是肯定的,当初虚报入宅搜查的人,后来得了重病,无钱买药,无奈之下,找我父母亲借钱。不料我父母亲非常慷慨,一下子给他二百元钱。当他接过二百元钱后,双眼湿润,嘴巴嚅动了半天讲不出半句话来。我母亲见状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要做的事,回去把身体养好!”我父亲也说:“去吧,抓紧看病买药!”
后来,我父母亲先后离世。我在改造了院子里,不忘种上梅树。每当梅花盛开时,就觉得父母亲没有走远!
今天,后院的梅花又要绽放了!
□作者:一分老人
□审核:叶维锡
□编辑:清溪客
扫码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matijina.com/mtjzy/789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