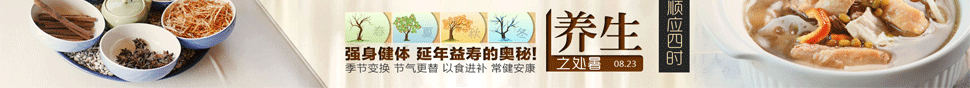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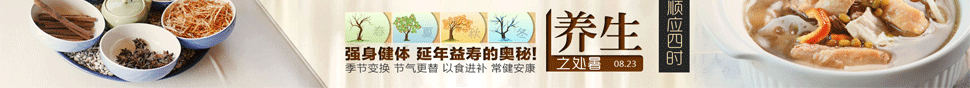
授权转自:深圳尚书吧
哲学园鸣谢
『旧时月色新派书香』昨天的活动回顾简要梳理和概括了辛德勇老师在《海昏侯新论》发布暨《海昏侯刘贺》精装本新书发布与读者分享会上的谈话,碍于体例,删去了很多论述细节,本篇是对上篇内容的扩展,除修改三五字外,补上了提问环节的问答,供不能到场的朋友们阅览。
▲辛德勇照片集锦吴忠平摄于尚书吧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做历史研究的,历史的曲折、复杂和回环动荡,是不以个人和每一代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其发展终究有必然趋势,它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千折百回必然走过去。在这个大背景下,我走入了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研究海昏侯刘贺实属偶然,今天,这两本新书就在这里跟各位朋友见面了,有的人可能还没来得及看,那我先从老书《海昏侯刘贺》谈起,和大家聊聊这两本书。
历史研究是以考古学资料为重要辅助的,海昏侯墓的发掘把刘贺推到大众眼前,那么,刘贺是怎样从今天的山东菏泽(故昌邑国)过函谷关进入关中长安做皇帝,又在27天后被遣回故国当高级囚徒,受严密监视;最后被汉宣帝册封至江西南昌做海昏侯,最终魂归江西?
其实我原来是做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在秦汉政区研究中偶然涉及西汉年号的问题。我发现“地节”这一年号很特别。《汉书·本纪》记载,汉宣帝时期,“本始”年号用了四年,由“本始四年”过渡到“地节元年”,由“地节四年”进入“元康元年”。但是发掘的汉代文物不是这样标记的。
这点上,王国维先生别具只眼,上世纪初,在仅看到少量敦煌出土汉简的情况下,凭着上面“本始六年”的字眼,敏锐觉察到其中必有异常。王国维先生之后,汉简成就最高的陈梦家先生在这个问题上遇到困扰,没有深究下去。到了年春节前后,西安市未央区出土了一大批西汉五铢钱陶范,上面出现了“本始五年”的文字,当时有一批古钱币学者和历史学者介入研究,但关于“地节”改元的问题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于是我带着问题开始查阅大量人物传记。
在翻看《汉书·宣帝本纪》时,我发现“地节二年”出现了重大政治变化,就在这一年,霍光病死,汉宣帝亲政。从年号入手,我转向了更广阔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梳理,最终追溯至汉武帝晚期,这就是《海昏侯刘贺》为什么从汉武帝写起的原因。
整个西汉的政治洪流是一条主线,它裹挟着刘贺走到历史舞台中央,让他攀上高峰,又跌落谷底。于是我思考,从汉武帝去世到汉宣帝亲政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很多细节在历史长河中慢慢流失,但通过对碎片化信息的串联拼凑,从权力视角对共通人性的把握,最终成了此书。这里要感谢三联书店张龙先生主动联系我出书。
这本书总体上说没有什么需要大改动的,但有一些内容上的补充调整。在《海昏侯刘贺》出版后,我就一些问题又陆续写了文章,将一些未及详论的内容以及存在争议或者新思考的问题,放进了《海昏侯新论》中。
《新论》第一篇讲刘贺和西汉中期宫廷政治,总体上是对《海昏侯刘贺》的浓缩。虽是浓缩却不简单,比如说赵婕妤的死因,《海昏侯刘贺》是参照《史记·外戚世家》的记载,认为武帝为防止“母少子壮”女主专政将其杀死。《新论》我采取了《汉书》记载,认为她是因受汉武帝冷落,抑郁而终。又比如刘贺进入未央宫后,导致霍光断然将其替换掉的原因,是因为他更换了长乐宫卫尉,这令霍光无法容忍。诸如此类的内容在《新论》都有补充。
有些内容是在《海昏侯刘贺》中写了简单结论,但是论证过程没有展开的。比如文献记载刘贺“四肢拘挛,膝痛不可伸”以至“两足不能相过”,我推测,刘贺的病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类风湿病,我的家乡在东北,那里风湿性关节炎发病率很高,但年轻时因为风湿性关节炎,导致“两足不能相过”,也就是后脚迈不过前脚是很少见的,一字之差,相去甚远。很多人说他是香瓜中毒而死,我觉得不是这样。
《新论》在旧有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着刘贺的墓园和墓室出土的文献文物,展开了一些新的论述,这些是《新论》的探讨重点。如海昏侯墓园的平面布局形态及其与汉长安城平面布局的关系、所谓"马蹄金"的政治文化意义及其与战国秦汉间金币形制演变的关系。
辛德勇老师签名钤印本
在都城布局问题上,中国古代城市都城构成要素中最重要的是皇宫,因此宫城、皇城的布局规划是研究重点。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在中国古代都城史研究上,复旦大学杨宽先生提出汉代“侧重西南”一说。往前追溯到秦,秦代后期也重西南角。往后看,隋代大兴城、唐代长安城,北宋开封城,以及明清宫城大致都位于都城中心。反对这种看法的刘庆柱先生认为汉长安城的修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先修一个个宫殿,再修外城的。
那么,汉代宫城位于西南角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还是主观性观念的缘故一直不明晰。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杨宽先生的观点,但苦于没有太好的例证。
年,部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馆展览时,我特意观察了海昏侯墓园平面,墓园是由一组墓葬构成的,海昏侯刘贺的墓室就位于西南隅,这印证了杨宽先生提到的汉长安城平面布局“重西南”的观点,我当时很激动,觉得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还在墓园平面示意图前傻乎乎地照了张相。
关于“重西南”的问题,我认为从汉到唐的都城建设在观念上存在着从“敬天”到“仿天”的过程。汉代宫城位于西南角,留出东北角致敬日轮和极星。到了隋唐,君主认为自己是天,要求别人对他礼敬。认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变化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背后是整体的天与人,人与社会的观念变化。这点以后有机会我会详细谈。
海昏侯墓最吸引大众眼球的就是那些黄澄澄的金子。关于出土的“马蹄金”,我认为它的正确名称是“褭蹏金”,“马蹄金”的称呼就让它从天马变成了凡马,失去了背后复杂的历史寓意。它本质是汉武帝通过其阴阳术数主观观念来体现政治统治的强烈象征符号,这里不详细展开。
那么,关于哪些是褭蹏金,哪些是麟趾金,过去一直争论不清,一直到十几年前还是这样。但随着海昏侯墓出土一大批褭蹏金和麟趾金,现在基本确定了形状较圆的是褭蹏金,像靴子一样的是麟趾金。
更重要的是,由这种特种纪念币带出的另一个问题:一般金币形制又是怎样?我发现,大金饼是十六两,小金饼在重量上是大金饼的十六分之一,十六两为一斤,在总结对比了安志敏、黄盛璋、张先得、杨君先生的研究后,我将圆形金币划分了五六种类型,得出结论:圆形金币的范式是由秦确立的。这篇文章是对中国早期货币史论的梳理,最早发表在《文史》上,构成了我的《新论》第10章。
《海昏侯新论》是一些专题文章的集结,可能没有《海昏侯刘贺》那么流畅,阅读时,有人可能会觉得我的文字稍显啰嗦,大量史料的引用令人感觉艰涩,但我仍然希望自己努力做到逻辑次序的清晰,因为历史研究本身需要有具体的支撑,将来有更加切实的材料可能会推翻现有的结论,但依据现有材料只能做到目前这样。
我也希望这两本书在社会文化和学术研究两方面,都能够对海昏侯相关问题的研究有实质性意义的推动。在《海昏侯新论》之后,有时间我还会继续做一些相关问题。
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东西,比如汉代墓牍,希望借此研究当时的文书制度;比如汉代常见的釭灯,我联想到了丝绸之路和张骞的“凿空”,由这牵扯出汉武帝河西四郡的开拓和设立年代。还有海昏侯墓室出现的那批简牍,这批简牍的研究难度是很大的,因为非常破碎。
总之,海昏侯和我一直相伴在一起,这次海昏侯墓园文物在深博的展出是非常难得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据说以后可能很难有了,但我希望海昏侯到处走,而我跟着海昏侯走。
好了,我的话,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
年6月23日下午
提问环节
问:老师好,我前两天去看了海昏侯展,有个问题一直很困惑,想跟您请教,我看到,不管什么尺寸的褭蹏金上面都写着“上”、“中”、“下”,看起来像是一套的,所以向您请教一下,这背后有什么含义吗?
答:这个问题非常好玩,但目前没有答案。我问过杨军先生,这些金子的成色和重量是不是有区别,杨先生告诉我是没有的。目前,我关于这点的一个非常不成熟的想法是:褭蹏金和麟趾金,作为具有特殊政治象征意义的金币,是人们在长安城或一个个大小诸侯王国里祭祀祖先时使用的,而“上”、“中”、“下”用来标记祭祀过程的不同步骤,像戏剧一样,第一幕为上。但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想,关于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杨君先生,他也说不清楚其中的含义,所以这个问题目前没办法解决。
问:老师好,我对于对霍光的第一印象最早是来自《三国演义》,在里面,霍光以一个忠臣或能臣形象出现。但是我在后来的书中看到的霍光已经是一个权臣形象了。我想问,在后世君主与臣子之间,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您如何评价霍光的行为?
答:霍光在后世君主与臣子中被如何看待,这一点我没有太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matijina.com/mtjcd/507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