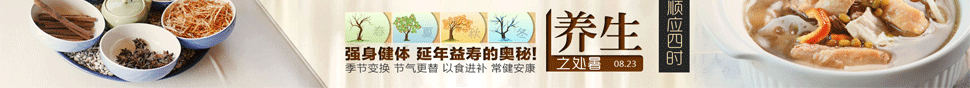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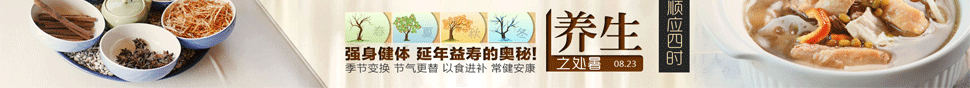
(年3月21日,CCTV-9)
年12月,已经持续了五年的海昏侯墓发掘工作进入内棺考古阶段,犹如一部悬疑小说,终于达到最后的高潮,令人回味无穷。
一大早,观西村村民就聚拢到附近的海昏侯墓考古工地,听说墓中那口已经一鸣惊人的棺木要搬家了,毕竟是他们让这座大墓免遭盗墓贼之手。如今,大墓的核心——内棺,终于要开启了。
为了更便于保护与研究,必须把它移到实验室中。区区几百米路,却走了两个小时。
玉佩(出土于主椁室);玉印(出土于主椁室)
国家文物局海昏侯墓专家组组长,信立祥:“根据汉代人的信仰以及我们多年来对汉墓发掘的经验,像这样高等级贵族的内棺里面会有大量的玉器,还有一些非常精巧、细致而昂贵的装饰品。另外呢,还有更值得我们期待的东西,就是直接标明墓主人身份的私印。这里边出土的文物将最后解开我们期待已久的关于海昏侯的历史之谜。”
第二天,所有人员到位,内棺即将开启,气氛有些肃然。考古人员首先要揭去主棺表面用来保湿防裂的宣纸。安放主棺的棺床带有木轮,便于下葬时推入墓穴。如今木轮犹在,主棺的高度却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棺中文物恐怕凶多吉少。人们嘴上不说,心中却七上八下。
“慢慢地……还能起点儿吗?”“还行。”“再给那边垫点儿东西,垫点小木块,再往上垫一垫。”“至少还要这么高。”“来块小的。”“那边顶着一点。”“可以啦!”
专家们却有些迫不及待。
“扶着点儿,扶住上面框架就可以。”“那不一定是。”“是不是金缕玉衣?”“六个,七个(玉璧)。左右各一把佩剑,那儿一把,这儿一把。”
硕大的玉璧瑕不掩瑜,精巧的漆盒鲜红欲滴,温润的玉佩一片冰心,环首刀把雄风犹在。然而,墓主人的骸骨却不见踪影。他到底是谁?!时间倏忽而过,宣纸重新盖上,喷水保湿。
第三天,工作继续。历经岁月与磨难的棺中文物混杂在淤泥中,大件器物尚能看出轮廓,微小物件则如沙里淘金。忽然,有人在满眼狼藉中发现一个小凸起:方形,似玉,刻痕朦胧,仿若文字。停顿,静止,人们似乎预感到它非同小可。由于死者尸骸已经在潮湿又失去密封的环境下“零落成泥碾作尘”了,专家们必须推断出遗体的位置以及它和那个小凸起的关系。在内棺南侧,人们发现一具盖在死者脸部的“玉覆面”。在它之下,有不少玉块,很可能是死者头下的玉枕。内棺中部这几块大型玉璧应该摆放在死者胸腹部。由此,遗骸的位置基本确定。而那枚小凸起和几个小物件恰恰位于死者腰部,很可能是腰带上的悬挂物,方便随时取用,其中就包括印章。
经过讨论,考古队决定对它进行谨慎提取。
“把它拿走,到时候去做上面的包含物。”“仔细看一下,这个争论好大。这是一个蟾蜍吗?还是……”
小心提取,果然不负众望。这是一枚汉代常见的方寸之印,印面边长2.1厘米,通高1.5厘米,玲珑剔透,用上等和田玉雕琢而成。玉面文字,阴刻篆书,左右等分,两个字正是考古人员和专家们期待依旧的答案——“刘贺”!它线条清晰,构图规整,方朴端重。五年春秋,人力物力,酸甜苦辣,终于水落石出,如愿以偿。虽然此前已经有许多墓主人的证据指向刘贺,但它们都抵不过这一枚小小的印章。西汉海昏侯墓,可以更加确切地改为“西汉海昏侯刘贺墓”了。
刘贺短暂的一生扮演了四种角色。从王到帝,又从帝归民,再由民封侯,犹如过山车大起大落,身不由己,这命数到底是怎样一个是非黑白?!
人们今天对刘贺的认知基本都源于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作者是东汉人班固。他出身史学世家,治学严谨,颇受皇帝赏识。因此,这部以尊重文献著称的《汉书》当属正史。那么《汉书》中的刘贺到底如何呢?班固说,昌邑王“动作多不正”“行污于庶人”等等,意思是不守规矩、胡作非为,还一意孤行。虽然少不成器,假如他能浪子回头,尚不至于一败涂地。
《汉书》详细记载了刘贺当皇帝后“荒淫迷惑,失帝王礼仪,乱汉制度”的罪状。诸如居丧期间与旧臣舞伎、酒肉嬉戏、吹拉弹唱,戏野猪、斗老虎,让下人乘坐太后的专用马车、自己则与先帝的宫女淫乱,一方面金玉绫罗、乱加封赏,一方面又诏书满天飞向各地征缴财物多达次,如此这般,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当时的情况下,西汉王朝走到这一步还没有出现过超过这种混乱的这个帝王。他是一种被选择上来的,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政治人物占据在这个地位上,可能大家会有疑问。”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杨哲峰:“这个东西最关键的一个字是‘孝’,突出了‘孝’的问题。尤其是和昭帝后宫的这些事情,这个是最要命的,这是为天下所不能容忍的(事情)。”
但也有学者提出另一种可能。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废黜刘贺的诏书里面没有举出任何一项具有实质性的、刘贺不配做皇帝的这样的内容,大多数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内容,这些内容都体现的是刘贺不太沉稳、不太成熟、不太符合礼仪规范。但表面上在诏书里列举的所有事情,都不足以决定他不能做皇帝,都是这样性质的东西。”
国家文物局海昏侯墓专家组组长,信立祥:“我认为呢,史书上,特别是《汉书》上对于刘贺本人的描绘和记载不可凭信。那么对于政治上的失败者,总要对他个人的道德、品质以及他的学养横加指责、横加罪名。所以我们好不足奇。”
东汉的班固与西汉刘贺相差不过一百多年,相关史料尚未遗失,改朝换代又降低了犯上的风险,《汉书》的可信度理应很高。但书是人写的,个人倾向在所难免。能够弥补这不足的,恰恰是沉埋于地下的历史遗存,用事实说话。
刘贺墓中,社会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matijina.com/mtjbm/9515.html

